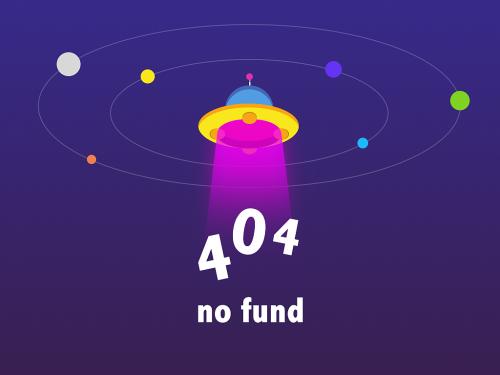□田耀东
春节的初二至元宵,是访人家最好的佳节。
腊月里,掸檐尘、贴春联,灶家菩萨擦得唇红齿白。炒花生炒豆、糖果糕点,腊鱼腊肉备齐了。家里干干净净、红红火火,桌子上也不空荡寒酸。
大姑娘小伙子穿上新衣服,再贫穷的人家也不显得落魄——用不着专门预备什么了。沙地人节俭惯了,办大事所以选在春节里。
一年之计在于春,春节里,什么事都要从长计议。访了人家、定了亲,生活就有目标。
春里在西山头搭一间七路头房,秋里叫木匠打一张花板床。或者,就在柜床上插个架子,嵌上花板,上面睡人,下面放粮食。
还有碗橱,桌子板凳、打桁凳、烧火凳,还有铁锹、钉耙、锄头铁搭,还有坛坛罐罐、碗筷汤勺,都要列入新一年的分家计划,都要一样一样地衔回来。庄稼人过日子,少一样就不行。
那时,没有电话,没有手机,电话线就连在番芋藤上,人与人之间交流少,婚姻的红线牵在介绍人手里。
介绍人都是菩萨心肠,是七大姑八大姨中受人尊重的长者。牵线前,先掂量一下门当户对:什么出身成分,什么文化,小伙子有什么手艺,姑娘长得漂不漂亮,性格像水、还是像火。
姑娘最关心的是小伙子看了是否会心跳,婆婆的性格,还有姑子妯娌是否好相处……这些七七八八,都要在介绍人心中斟酌一番,然后蟑螂配灶鸡,帅哥配美女。好的介绍人,大都是呱呱叫的妇女队长,个个能说会道。
挑选的双方,自然都是八九不离十。访人家,就是双方再对一对眼缘,实人实地考察一番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双方都对访人家很重视——努力摆出最好的姿势。
上世纪的婚姻,都是一竿子插到底,娶了一个,嫁了一个,就是一辈子。纵然将来有变数,也不能怪介绍人——你自己也去看的,眼睛睁得大大的,我不过吃了你一只蹄髈、两瓶洋河!
访人家可以是姑娘去小伙子的家,也可以是小伙子去姑娘的家,但多数是姑娘去小伙子家先看。因为她要在那里生活一辈子,和那个人,在那个地方,还有公公婆婆、姑子妯娌、大伯小叔。
特别是那个人,访人家前,有的见过面,有的没有见过。如果一见就脸红心跳,旁的一切都好说。如果一见平平的,其他条件加上去,想想也可以过一辈子,也就定下来了。
小伙子去访姑娘家,不但看姑娘,还要看丈母娘——娶媳妇看娘,女儿是娘的翻版。丈母娘干净利索,温言细语,女儿也错不到哪里去。
去姑娘家,不但小伙子和介绍人去,往往能干的小姑子也自告奋勇地跟了去,未来的准婆婆也跟了去——看姑娘纺的纱、织的布、纳在鞋底上的花样子,都能看出姑娘的心灵手巧。
姑娘去小伙子家访人家,看小伙子是否壮实,五官端正,手脚粗壮,目光锐利温和,声音洪亮无娘娘腔,举止得当应答是否自如。
如果小伙子还是泥匠、木匠,有一门手艺,门楣上贴着“光荣之家”的红字,墙上挂着部队的奖状,丈母娘心里便先认可了,拿眼睛偷偷地瞟小伙子——丈母娘看女婿,越看越有趣。
姑娘低下头,红着脸,摆弄着长长的辫子梢,坐下来腼腆地喝着红糖茶——心里也认可了。
细心的丈母娘一面喝茶一面端详亲家母的言行举动,眉眼善不善,腮上是横肉还是安善如菩萨。
抬头看小伙子家的房子,是七路头还是五路头,是四米八还是四米。屋檐高不高,木头粗不粗,椽子是杉木还是树棍子,是青砖望板还是芦头笆面。
门窗结实不结实,玻璃擦得亮不亮。地面是砖铺还是泥地面,山头上有梁柱还仅仅是红砖墙。
灶口头理得清清爽爽还是碎屑里藏着蟑螂,壁脚壁眼里是否扫得干干净净还是门背后有灰尘。灶山上抱着红鲤鱼的胖娃娃笑得好看还是额角头上沾了油腻。
准婆婆会带着介绍人和准亲家母去看家具:这是老木柜,不是嫩木头,这是柜床,全是杉木板打的。这口大缸是红釉的,摸上去滴滴滑。这张桌子、四张椿凳,还是他爷爷结婚那年种的椿树打的,你看多厚重结实,刚上了小清油。这都是留给小三子结婚用的……
小姑子还会带未来的嫂嫂去看猪圈,去看圈里的肥猪。猪圈旁边是羊棚,公羊母羊小羊一大群,看见姑娘一齐站起来鞠躬。
羊棚旁边是鸡舍,红壳蛋滚在麦草里。临河一片竹林,竹林里一座鸭舍,鸭子在竹林追逐一番下河去,扇起翅膀嘎嘎地叫,河边几只白生生的鸭蛋。
鸡窝前面是柴堆,棉花秸秆、玉米秸头、乌秋根这些硬柴码得整整齐齐。
河沿上的红梅花刚绽出骨朵,含苞待放,桃树、梨树已整过枝,疏疏朗朗、厚积薄发、生机勃勃。
菜地里的青菜菠菜已罩上塑料薄膜,黄芽菜裹得圆墩墩,盖着瓦片防冻防雪,棵棵结实得可以当矮凳坐……
小姑子低眉顺眼、俏皮殷勤,笑盈盈地给未来的嫂嫂递瓜子、剥糖块,给姑娘和来人端茶添水,悄悄地贴着她哥的耳朵说,哥呀,你有福了!
从此她一心一意等待嫁期,在娘家缝衣做鞋备嫁妆。鞋底扎了十八双,袜底绣了廿八对,芦菲花布带两匹,蓝印花布剪三段,零头布卷起来,红着脸,偷偷地比画着给娃娃缝小衣、做虎头鞋。
从此恩恩爱爱、酸酸甜甜,风风雨雨、青丝白头,桃面红花直到脸面如芦花婆鞋,一辈子就这么手携手地过了。
而这一切,往往决定于春节里的那次访人家。